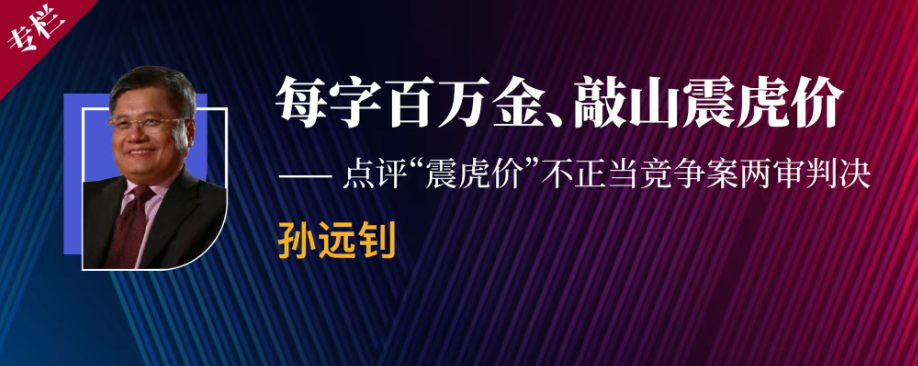
每字百万金、敲山震虎价—— 点评“震虎价”不正当竞争案两审判决
目次
一、司法判决
二、可能适用的法规
三、问题与商榷
四、结论
一、司法判决
图片来源:京东汽车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25年7月21日出台了“上海阑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原判,认为被告京东汽车的“震虎价”系列宣传文案(见上图)对被告的“途虎养车”品牌构成商业诋毁和虚假宣传两类不正当竞争,应赔偿500万元经济损失加上46,800元的案件受理费以及赔礼道歉等。[1]法院表示,被告使用“震虎价”为名从事低价营消活动,“明显带有贬损市场竞争对手阑途公司的主观意图,……编造、传播阑途公司为不良市场经营主体的虚假信息及误导性信息,损害了竞争对手(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此外,这个低价促销活动,“其行为脉络是以虚假信息及误导性信息诋毁阑途公司,损害其商业信誉及商品声誉,误导阑途公司原有客户脱离或阻止产生新的客户,以此为基础,通过价格折扣、比对,吸引、拉拢这些客户,达到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竞争目的,其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也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
为了强化论述,法院另表示,“并非所有消费者对于其购买的服务或商品都会进行比价,而〔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三种不符合其承诺的页面标价,这表明这部分消费者的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广告宣传往往会有适度的夸张,但其边界必须止于引人误解。”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认定,表示“作为行业内知名企业,通过其运营的各类网络平台和线下进行的宣传活动,对阑途公司贬损丑化程度深、指向性明确,主观恶意程度较大,不正当竞争行为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超过一年且持续至诉讼期间,对阑途公司商誉造成的损害较大。”法院并对被告抗辩被告的收益不减反增不予支持,认为原告因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遭受了损害,〔原告〕的营收情况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与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无必然关系”。
二、可能适用的法规
可能與本案情形直接有關的法规包括下列6个条款:
現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2025年10月15日第三次修正开始施行后将改列为第9条,内容不变):“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 主体是经营者,具体行为是直接或间接对自己商品从事虚假误导性的宣传或误导,即通称的“虚假宣传”。
同法第11条(新法改列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 主体仍是经营者,具体行为则是直接或间接对他人商品从事虚假、误导性的宣传或误导,即通称的“商业诋毁”。
如经营者对自己的商品从事虚假宣传,同时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誉,可能构成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两者的竞合。两种侵害行为可以并存,不相互排斥。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条款只规定了对“商品”的虚假误导,可否也同样适用于“服务”,则不无疑问。鉴于当前商品与服务在绝大多数的市场交易情形已经融合为一,如商品的售后服务、服务当中对特定商品的使用和推荐等等,《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同样适用于服务。未来的立法恐需对此厘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反法解释》)[2]第16条:“经营者在商业宣传过程中,提供不真实的商品相关信息,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的商业宣传。”
同解释第17条:“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一)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
(二)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
(三)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
(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进行认定。”
同解释第18条:“当事人主张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并请求赔偿损失的,应当举证证明其因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受到损失。”
同解释第19条:“当事人主张经营者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商业诋毁行为的,应当举证证明其为该商业诋毁行为的特定损害对象。”
三、问题与商榷
(一)商业诋毁
一审法院开宗明义表示,“本案中,‘震虎价’的‘虎’是否指向阑途公司是争议焦点的核心所在,也是认定被诉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的关键。”意味着只要能够确立被告使用“震虎价”的指向,基本上已几乎可以认定使用这三个字就构成了商业诋毁。
因此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商业诋毁”的定义与内涵究竟为何?尤其是当厂家之间展开价格战时,只涉及对价格的“指控”、“挖苦”、“嘲讽”等表述可否构成“商业诋毁”?
参酌、对照一些具有指标性国家对商业诋毁的规制,可发现基本上的定义和构成要件都大致雷同。[3]其中的一个关键要件是,必须由主张构成诋毁的一方举证,显示被告所散布的是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亦即对其商品的描述不符客观事实。就此而论,只要(1)价格战不涉及对竞争对手商品或服务的明显指向;而且(二)不涉及对该商品或服务进行虚罔不实的描述,纵使一些用字遣词或有令人不快、认为低俗甚至恶心之处,只要不完全符合法定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构成商业诋毁。这也是知识产权必须严谨依循《法定原则》的体现。
那么被告使用“震虎价”是否构成商业诋毁?这个用字(词)显然借用了“敲山震虎”的成语,意在让消费者与原告的“途虎养车”品牌产生联想。所以法院判认这个营销活动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是正确的。
法院继而表示,“虎”字“既可比喻威武勇猛而具有褒扬之义,又可比喻残酷凶暴而具有贬损之义。”继而依据被告京东公司在庭审对对使用这三个字的构思由来提供的解释,直接以自身的心证判定是赋予了贬损之意。
二审法院正确指出了“本案需要判断的是在特定场景下使用‘震虎价’的表述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商业诋毁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直接指明诋毁的具体对象的名称,但指向的对象应当是可辨别的”。
但是从“震虎价”这三个字的组合本身和使用的语境而言,同样可以解读为,被告做为“汽车后市场”的入行新手,依然把原告的品牌称之为“虎”,不但不存在对原告的产品的贬抑或讥讽,反而认知了其竞争者至少是个“虎”级的对手(依据2023年年底的数据,途虎已连续13年是国内最大的轮胎零售商和服务商[4]),想单挑市场里最大的竞争者,自然不好对付,于是展开削价竞争,想要震撼那只最大的“虎”。
换句话说,“震虎价”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含意,且可能一语数关,不同的含意之间并不相互排斥。法院所应依据的,是一般消费者的合理解读。[5]从二审判决书提供的证据和说明,只能看到双方介入的,是一场价格竞争;没有触及及对原告提供服务的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从事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告欺骗或误导了消费者。因此,法院至少应推定“震虎价”本身并不涉及商业诋毁。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则,原告自可反证此一推定,且应承担相关的举证责任。
图片来源:微博
遗憾的是,判决书当中没有对一般消费者对此如何认知的相关证据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例如,二审判决书当中仅简单提及了被告名为《京东养车震‘虎’价》宣传视频评论区的若干评论。但这几个评论究竟能否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认知和反应,恐怕还有待商榷;反过来说,即使被引述的几个“网友评论”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例示,也可明显看到评论的撰写者能相当清楚辨明这无非就是一场价格战,因此完全没有看到对原告商品或服务质量的评价或有任何贬抑的表述,也恰恰否定了构成商业诋毁。[6]至于原告所指,被告把印有“京东618震虎价”“京东养车618震虎价”字样的宣传大巴,分别在原告位于杭州市的一家门店(见上图)和位于上海市的营业所在园区开展宣传活动等或可被认为属于过分、挑衅、有道德瑕疵的商业竞争手段,但终究还不足以构成损害原告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的虚假或误导信息,也就不存在“商业诋毁”不正当(不法)竞争行为。
既然认定的关键应是消费者的一般认知。被告在设计“震虎价”的口号时究竟是如何构思其含意与全案的事实认定完全无关,法院也不应依其主观心证在此基础上迳行对“震虎价”选定了负面的价值评断并直接结论。本案的两审法院对全案的核心争议从一开始未能固守住法定要件或设定的标准,或因受到了本案特定事实与“损人利己”概念认知的影响(详后述),先入为主,殊为可惜!
再就“震虎价”三个字而言,从判决书描述的既有证据以观,双方的争议完全聚焦在价格竞争,并未涉及任何对原告商品或服务“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所以不符《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的要件,难以指摘构成“商业诋毁”。然而法院却仅从对“虎”字的指向和负面含意就直接推导出被告方“明显带有贬损市场竞争对手阑途公司的主观意图,……编造、传播阑途公司为不良市场经营主体的虚假信息及误导性信息”,委实欠缺说服力。
至于与被告“震虎价”相关的其他周边文案及附带表述,无论是文字、图像或视频,同样需要从一般消费者认知的视角分别审视,不可一概而论。原告也应负提出因果关系与消费者认知的举证之责。
总之,原告想从一个价格竞争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确有相当的难度。毕竟用两种价格“碰瓷”本质上就在直接反应一个特定事实,尤其如本案,入行的新手试图挑战最大的市场持份者,只要不涉及编造、传播对手商品或服务的虚假信息(因为可以轻易查证核实),就不能视为商业诋毁。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尤须谨小慎微,严守法定要件,否则任何削价营销,尤其是所谓“破坏性的竞争”都可能动辄得咎,这样反易引起“寒蝉效应”,导致市场裹足。
(二)虚假宣传
前已提及,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是,共同被告“实施的‘震虎价’低价营销活动,其行为脉络是以虚假信息及误导性信息诋毁阑途公司,损害其商业信誉及商品声誉,误导阑途公司原有客户脱离或阻止产生新的客户,以此为基础,通过价格折扣、比对,吸引、拉拢这些客户,达到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竞争目的,其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原告〕现所主张涉嫌虚假宣传行为实为该整体不法行为的一部分,行为意图和目的具有一致性。”
问题是,依据現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新法第9条,内容不变),构成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必须是关于“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其中完全没有提及“价格”。究竟“价格”应否被纳入完全取决于该条款使用的“等”字应给予如何的解释 —— 只是做为闭环列举,但不具任何实质意义的修辞(狭义说或否定观点)?抑或是开放、不完全的列举(广义说或肯定观点)?早期曾有司法判决对《著作权法》条款中的“等”字采取了广义说。[7]不过那个判决的特殊背景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WIPO)已于该判决出台前(1996年12月20日)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两个与互联网相关的重要国际著作权保护公约(条约),正式确认了“公开传输权”(Right of Communications to the Public,等同于现行法规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国政府当时正展开并积极推动加入这两个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工作(其中包括了保护知识产权的《TRIPS协定》),国内的经济、科技发展也开始进入腾飞的阶段,在内、外需求强力加持的状况下,法院面临法律条款滞后的“尴尬”,只能另辟蹊径,不寻常地扩张解释了当时《著作权法》的适用范围,形同法官造法。
本案再次发生了对法律条款当中的“等”字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但相关的背景和环境却已然大不相同。彼时立法尚未完备,又迫切需要充实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与国际规则接轨,法院例外地采取扩张解释是一时不得已的权宜。现今则是相关立法基本皆已到位,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超国际标准的保护,因此关系到市场机制的法规,法院不宜轻易扩张解释,引发疑虑和不知所从的“寒蝉效应”,而应回归到对私人(自然人或法人)的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拉丁语:Quod non est prohibitum, permisum est;英语:Everything which is not forbidden is allowed)的基本法则。[8]
不把价格纳入到此一条款之中本是正确的立法政策,没有任何理由需要通过司法判决或解释予以扩张改变。因为价格在本质上是动态的,随时会因市场状况的变化产生变动。某甲为了同某乙竞争,推出的价格很可能会刺激某乙必须快速反应和跟进,甚至更进一步削价以维持自身的竞争力。所以也许昨天是正确的信息因为一方当事人有所反应,今天跟进调降了价格,技术上就变成了不正确的信息。可否因此就认定发动价格战的一方构成虚假、诋毁和(或)误导,显然大有疑问。这表示,即使能以价格竞比做为审判的考量,必须特别审慎,尤其要确定是以苹果评比另一个同时同样的苹果。毕竟只从“比价”来论断是否涉及虚假误导,本身已蕴含了巨大的逻辑风险,稍有不慎,挂漏了本应加入或纳入了本不该加入的因素就容易产生谬误。更何况价格在此本来就不是应被纳入考量的因素。
一审判决在欠缺相关举证、适用标准错误的“基础”上迳自认定共同被告的“震虎价”已构成虚假、诋毁和(或)误导,继而判认,共同被告“通过价格折扣、比对,吸引、拉拢客户”等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继而使用了相当篇幅从被告的广告文案不符合《广告法》的要求,没有表明其公布的销售页面价格是按实际成交价计算,因此不够准确、清楚、明白,被告也没有举证消费者获得了按实际成交价结算的相关信息,便断言消费者显然会因此遭受损害。法院更进一步指称,并非所有消费者对于其购买的服务或商品都会进行比价,也就表明了这部分消费者的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并由此直接做出了共同被告“发布的商品降价承诺信息与事实不符,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的结论。一审判决的论述获得了二审法院的完全引用和认可。
然而这段论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反不正当竞争法》最终的目的固然蕴含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立法目的),但是该法的内涵终究是规制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行为(第2条第2款的定义),与消费者无关。消费者只是反不正当竞争立法政策上的间接受益者。因此,法院在此应检视的不是消费者是否受到了损害,而是经营者之间的加害与损害因果关系,尤其不能因有消费者可能会受到损害就与一方经营者受到损害直接划上等号。法院的论述有概念置换的嫌疑。消费者是否受损,如何获得救济,自应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不可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要件和认定混为一谈。
其次,前已提及,价格从来不宜、也不应是法院在本案关于虚假宣传部分需要考虑的因素。[9]即使被纳入考量,法院必须依循的标准还是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这是认定标准,与上述不考虑消费者是否受损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然而当法院刻意强调“并非所有消费者对于其购买的服务或商品都会进行比价”,因此权益可能会受损时,实已悖离了此一标准,自陷到一个谬误:是否只要有任何消费者没有或不知如何比价,提出削价竞争的一方经营者就会立即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果答案为肯定,如此轻易、动辄得咎,又如何鼓励市场竞争?如果答案为否定,那么究竟要有多少或多高比例的消费者不知如何比价才会构成“虚假”宣传(最低门槛)?这就落入了“数字门槛”的陷阱,实际上根本无解,且大幅弱化了判决的立论基础。所以必须回到“一般消费者认知”的标准,无涉任何量化分析。
第三,判决书这句“并非所有消费者对于其购买的服务或商品都会进行比价”透露出法院至少把大部分(“并非所有”实为“多数”的潜台词)消费者推定是或接近“消费文盲”,没有甄别广告夸张宣传的能力,因此一方面虽然认知“广告宣传往往会有适度的夸张”,他方面又表示“但其边界必须止于引人误解”,也就需要法院更大程度地介入和“矫正”,以达到法官自认符合“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这实际上法院是让自己陷入了“裁判兼球员”的角色混淆。消费者会不会自行比对价格根本不是法院应去关切或操心的问题。司法的头号天条是“不告不理”。法院只能凭据当事人的举证来判定一般消费者是如何认知,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结论。
第四,维系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政策是鼓励竞争。价格竞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质上便包含了程度不一,“通过价格折扣、比对,吸引、拉拢客户”的行为。缘何这些典型的降价竞争行为却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固然对应所谓“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已成为当前的重要政策指针,[10]但实与不正当竞争指控当中的虚假宣传没有直接的关系。既不是一个法律专有名称,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无论是否被贴上“内卷式”的标签,削价竞争并不当然违法,即使涉及掠夺性订价还是反垄断当中滥用市场地位,并非不正当竞争的问题。[11]法院必须依法论法,一码归一码,严谨依据可适用的法定要件和个别案件的具体事证分别论断。
两审法院各自使用了一定的篇幅讨论共同被告宣布的5%价格折扣不是按实际成交价格计算(或结算)以及没有告知消费者如价格高于原告将会退款。二审法院进一步表示,在此一宣传场景下,消费者会误认为共同被告的“震虎价”一定会比原告低5%,而且即使共同被告所称的“价高退款”属实,也不影响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会产生误解,因此还是判认构成欺骗、误导等虚假宣传。法院没有解释或说明所谓的“特定场景”是指什么,却旋即做了一个臆测性的推导:“如果上诉人同时告知消费者‘价格比友商低’和‘价高退款’,则消费者亦可能不会选择与上诉人进行交易。”然而实际的状况果真会如此么?即使真有这种可能就足以排除其他的各种可能么?例如,现时拥有(或驾驶)汽车的人几乎皆使用智能手机(许多汽车本身也提供了智能配件),随时可让使用者(消费者)通过行动网络便利的查询、比对各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因此已成为当前无数消费者的习惯性操作(货比三家)。如消费者查到了更低的价格时通常会当场提出质疑。如果厂家愿意同价跟进甚至给出更低的价格,消费者才可能愿意购买或使用该厂家的商品或服务。换句话说,法院千万不能低估了消费者的能耐,更不能以偏盖全。[12]
依据两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共同被告于2023年9月14日对其养车产品和服务推出名为“震虎价”的营销活动时,还没有提到“5%”的数值。共同被告选择在当天推出降价,明显为了对应原告同日启动招股,准备在香港证券交易市场上市。5%的出现,则是途虎养车于同年9月26日在香港股市正式上市当天,由京东零售汽车事业部总裁缪钦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发文“加码”而来。[13]换句话说,即使容许把价格竞比纳入考量,法院用事后才发生的状况推导之前的意图,尤其因此认定“震虎价”的名称本身已构成虚假宣传,恐怕反成倒果为因、本末倒置了。
总之,两审法院在虚假宣传的认定部分也有许多必须再做商榷之处,包括适用的法律条款具体范围还有待明确,对关键因素的考量、逻辑推导与相关举证都有相当大的瑕疵或不足。此外,根据现有的事证,尤其在适用一般消费者的认知做为标准时,共同被告的一些行为或有令人认为嚣张、过分和嫌恶之处,在没有更多的事证之前,还不足以直接判定构成违法虚假宣传。
(三)“损人利己”
归根结底,两审法院之所以会如此判决,背后的思维主轴显然受到了“损人利己”的认知导引。一旦法院在形成心证时有了这样的认定,涉诉的行为基本上就很容易被定性为非法或构成不正当竞争了。这个基本思路与之前若干具有指标性的司法判决可说是相当一致的。[14]
问题是,竞争的本质,固然不排除偶而会出现“利人利己”的情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不同程度的“损人利己”(挖掘他人既有的市场持份成为自身的市场自然意味着对他人的既得利益造成了损失)。所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规定的基本法则,并非只要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一旦受损就可以提出侵权主张,还必须以被告行为构成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为前提。市场竞争如同一场“中国跳棋”比赛(棋盘格式如上图),不过不再是三方,而是多方参与,路径与形式更加复杂的环境,但基本的竞赛规则却有些类似:有时一方可以藉由他方开创的路径找到机会,替自己塑造出一个捷径,能更快速的达到目标;但有时他方也会因为本身的需求或利益,把自己的路径给堵上了,于是只能另起炉灶,寻求他途。只要没有违反竞赛规则,就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竞争也如同开车上路,有时别人有心无意之间可能帮自己开了道,也有可能挡了自己的路,但这都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至少在水平竞争的情形)。既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法益(直接保护)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间接保护),只要被告对其产品或服务没有通过强暴、胁迫、欺诈或误导方式让消费者购买或使用,纵使有道德瑕疵,仍不可因为产生了“损人利己”的现象就迳行判定构成违法行为。
所以与此相关且至关重要的,是因果关系举证。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则和要求,原告应负相关的举证责任。[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16]第90条进一步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然而本案却出现了颇为“吊诡”的现象。基本上没有看到原告关于这方面的实质举证,二审判决也几乎没有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只用了一小段文句简单做结带过:“阑途公司因被侵权所受到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确定,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阑途公司商誉、被诉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以及阑途公司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定阑途公司的经济损失。”
倒是共同被告方面举证主张,原告自“震虎价”的营销活动开始后,截至2024年底(共1年3个月),其业绩收益始终呈现上升,因此并未因被告的竞价活动遭受损失。对此,二审法院也仅简单表示,“被上诉人的营收情况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与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无必然关系,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二审法院并抄录了一审法院的见解:“需要指出的是,阑途公司因〔共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遭受了损害,阑途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上升与损失因此并不存在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共同被告〕的辩解并非正当理由,……”
“营收情况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与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无必然关系”基本上是成立的,因为随着汽车后市场的不断扩大,业绩的成长的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掉了所受损失(如果的确发生了损失的话)。[17]但也同样表示在特定的案件仍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也就需要当事人提供更多相关的证据来帮助厘清。例如,各主要竞争者之间的市场持份变化、相关市场持份本身的实际成长状态、各当事人对市场和本身业绩的成长预期、相关消费者对此一削价竞争的反应所从事的实证调研和分析以及在展开“震虎价”的营销活动前后,共同被告自身业绩的变化等等。然而从两审的判决书都没有看到这些基本的举证和分析,反而更让判决的论述与结论显得失之草率;再加上法院最终迳自酌定以法定最高额度作为损害赔偿金额,更有恣意之嫌,对公信造成不良影响。[18]
参酌国外的司法实践,例如在美国和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要举证存在事实因果关系(causation-in-fact),通常使用“若非测试法”(but for test)。即,“若非〔被告〕从事了如何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原告〕便不会有如何的损失”,其反面意义是,需要论证如果没有被告的行为,原告指称遭到的损害是否依然会发生。无论如何,原告首先必须指证,究竟是遭到了如何的损害,不能因有举证难度就含糊其词、笼统虚无。除了事实因果关系,原告还需同时举证存在法定因果或近因关系(legal or proximate causation,类似于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adequate cause),即其遭受损失最直截或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被告的行为。这是为了排除各种没有直接影响或间接的“干扰”因素而设,以确保特定侵害行为与所受损害之间确实具有足够接近或相当的关联从而应受法律归责,包括是否为可预见的损害[19](foreseeable harm)。法院也应透过这些举证确定本案的责任成立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前提自然是确实发生了侵害)。[20]
四、结论
法院必须从潜意识当中设法摒除只要凭感觉发生了“损人利己”的状况就先入为主,概括认定当事人行为构成违法,然后再设法从既有的法规当中设法找出能够对应适用的条款。当涉及价格的问题和分析时,尤其必须明确掌握不正当竞争主要是通过严谨的法定性原则对经营者既有的行为给予适法性评价,反垄断主要则是通过经济分析对价格制定和输出控制的反竞争性评价。两者蕴含了不同的分际与分析,还经常会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产生竞合,千万不能混淆,否则反易对自身的判决论述造成误导、陷入误区。
如果经过研判,认为确实发生了侵害行为并造成损失(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明确指证具体的损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适当的损害赔偿金额,不能想方设法一意推给法院,只凭法官个人有限的直观和臆测(美其名为“心证”),欠缺各种周边与配套因素的综合考量,就“酌定”了在一个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容易导致市场难以适从,深怕动辄得咎,引起所谓的“寒蝉效应”。
依据两审判决书陈述的事实并审慎检视相关的法规条款,本案无论如何都难以认定构成商业诋毁。至于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则端看司法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等”字要作何解释(广义或狭义)。基于法定原则的要求,建议法院应采狭义解释为妥。无论如何,双方的举证,尤其在真正的关键问题方面,可谓明显不足,法院的论述分析也有不少地方有失之草率或颇值商榷之处,尤其与全案判决攸关,应适用“一般消费者认知”的标准,必须特别阐明,也让市场未来的操作有所依凭。因此,如败诉方未提出再审请求,谨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应依《民事诉讼法》第209条主动提审或指令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再审。
来源:京东汽车公司
本案二审判决出台后,败诉方京东汽车等随即停用了“震虎价”,但又旋即发动了一个全网征名的活动,寻求替代名称,于是又掀起了一波网络关注与热搜;并宣布将持续以50亿元来自京东集团的补贴支撑这场价格竞争,将“震虎价”改名为“震骨价”,还另取了“低价震骨,补贴不「唬」”的口号(见上图)。从某个视角而言,这个诉讼等于替京东汽车变相做了公关,虽是表面上的败诉方,却让整个削价竞争活动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关注和知名度。对京东而言,相关的诉讼、律师费用也形同公关开支,表面上“震虎价”3个字500万元的高额赔偿(等于每个字要赔付166.67万元)相较于平常的各种广告、行销费用反成了九牛一毛。
目前还不确定途虎养车是否会针对“震骨价”另行提告。假定双方再次发生争讼,“震骨价”是否仍会被法院视为换汤不换药,打“擦边球”,继续依原先的判决理由认为构成商业诋毁和虚假宣传还未可知。但至少可确定的是,京东汽车方面这回已先打了“预防针”,去除了一枚可能导致爆炸的引信,可宣称“震骨价”本身已不再具有任何的指向性。这是否会震动法院立论的基础和框架,还有待后续发展给出答案。
总之,法院在本案的两审判决恐怕先入为主,受到“损人利己就是坏”的认知左右,误导自己在先、又未严格依据法律条款所定要件,扩张适用、推导加上臆测,包括看低了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却保护过当,判决“震虎价”三个字构成误导,其中的多个瑕疵亟需通过再审更正。500万元的赔偿对京东公司而言,显然未能达到“伤筋错骨”的成效。然而对于其他的厂家而言,未来究应依据如何的标准、因果关系举证来推导是否构成商业诋毁与虚假宣传,却恐怕的确产生了“敲山震虎”般的摇撼!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2025)沪73民终33号(2025年7月21日)
【2】法释〔2022〕9号(2022年3月16日)。
【3】例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误导性商业实践),参见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WG), §5 Irreführende geschäftliche Handlungen;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44-48a条,参见California Civil Code §§ 44-48a。
【4】依据途虎2023年的财务报表,该公司当年经调整后的净利润为4.8亿。在营业收入的项下,汽车轮胎和底盘零部件、汽车保养分别占比40.8%和36.3%,而加盟收入占比仅5.4%。虽然拥有近6000家加盟店,覆盖了全国332个城市,该公司主要的收益来自通过自身供应链的销售和服务。虽然营收规模只有百亿,途虎自2010年起在汽车售后市场企业连续13年位居全国规模第一。参见再造一个京东,从“震虎”开始,《商业黑板报》,2024年6月24日,载于《维科网‧通信》,https://tele.ofweek.com/2024-06/ART-8320510-8500-30638516.html。
【5】《反法解释》第17条第2款;另参见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4)款(“在评价与消费者有关的商业实践时,应参酌一般消费者〔的认知和反应〕,如该商业实践是针对特定消费群体时,应参酌该群体的一般成员。……”其原文为:“Bei der Beurteilung von geschäftlichen Handlungen gegenüber Verbrauchern ist auf den durchschnittlichen Verbraucher oder, wenn sich die geschäftliche Handlung an eine bestimmte Gruppe von Verbrauchern wendet, auf ein durchschnittliches Mitglied dieser Gruppe abzustellen….”)。
【6】判决书列出、唯一可能牵涉到商业诋毁的只有一个评论:“等死吧,烂途虎,被震虎价震死”。但这里还是针对价格而言。
【7】“王蒙等六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在线”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1999〕海知初字第57号(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14日开庭审理(二审)并当庭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法院认为,当时的《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对作品使用方式的规定最后使用“等”字表示并非穷尽列举,还有其他的方式,因此未经许可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的作品也应构成构成侵权行为。
【8】Glanville Williams, The Concept of Legal Liberty, 56 Columbia Law Review 1129 (1956); John Laws, The Rule of Law: The Presumption of Liberty and Justice.22 Judicial Review 365 (2017).
【9】需要考虑价格的,主要是依据《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以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启动的监管、调查与司法诉讼。
【10】从一般特征而言,“内卷式”竞争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诸如低价、同质化和宣传营销的“逐底”竞争。参见“内卷式”竞争的突出表现和主要危害有哪些?,《求是网》,2025年7月9日,载于http://www.qstheory.cn/20250709/e92b12b140754c968a1743c3e12f9e0f/c.html(本文仅以“整体收益增长”做为衡量竞争行为是否属于“恶性”恐怕还有待商榷,详见注11);陈石,正确认识和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思想纵横),《人民日报》,2024年10月17日,第9版。
【11】一般而言,低价可促进竞争,有利于消费者,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形并不违法。只有当使用低于成本的价格(below-cost pricing,也称为“掠夺性订价”(predatory pricing))让具有市场支配力的一方足以迫其竞争对手退出市场(限制或排除竞争),然后再提升价格并维持相当的时间的,才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垄断行为。参见《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2)项(“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本案共同被告(京东公司)虽然具有雄厚的财力,但做为汽车售后市场的新近竞争者,本身不具有任何对相关市场的支配力,因此显然不符合此一规定的要件。
【12】二审法院一直到检视被告的价格是否果真比原告要低5%时,才首次正确的表示,“宣传用语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应根据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已有的认知经验,并结合具体场景进行判断。”然而随后的分析,却又明显地悖离了此一原则。详见后述。
【13】其贴文内容为:“恭喜友商挂牌上市,让更多人关注到汽车后市场。近期,大家也看到京东养车推出了‘震虎价’,在此我想邀请大家一起监督,所有‘震虎价’商品都要比友商低5%!同时,京东养车承诺,将坚持大牌低价、品质服务、正道成功,决不牺牲消费者利益来换取利润’”。参见二审判决书(四、其他相关事实第一段论述);另参见王玮,途虎上市,京东推出“震虎价”,养车行业“价格战”将打响?,《南都N视频APP/南都智行》,2023年9月27日,载于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30927853495.html。审视这个贴文的内容和语境,京东养车显然没有直接保证所有的标示价格必然已经比途虎养车要低5%,而是“邀请”消费者共同监督,以确保最终能获得低5%的价格。因此,即使没有倒果为因与本末倒置的问题,法院在判决书当中使用相当篇幅聚焦在这个数值的分析上,想以此来扣住并支持构成“虚假宣传”的指控,本身已是非常勉强和薄弱的推理论述。
【14】例如,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诉贝壳网际(北京)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案(“猎豹浏览器屏蔽视频广告”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民事判决,(2014)一中民终字第3283号,2015年2月13日(“竞争关系的存在是判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前提条件。……竞争关系的构成不取决于经营者之间是否属于同业竞争,亦不取决于是否属于现实存在的竞争,而应取决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是否具有‘损人利已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仅具有对其他经营者的经营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且该经营者同时会基于这一行为而获得现实或潜在的经营利益,则可以认定二者具有竞争关系。”);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极科极客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极路由屏蔽视频广告”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民事判决,(2014)京知民终字第79号,2014年9月12日(“……在互联网时代,判断经营者之间有无竞争关系,应着眼于经营者的具体行为,分析其行为是否损害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利益。本案被控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极科极客公司综合利用‘屏蔽视频广告’插件和‘极路由’路由器屏蔽爱奇艺网站视频的片前广告,此行为必将吸引爱奇艺网站的用户采用上述方法屏蔽该站视频片前广告,从而增加极科极客公司的商业利益,减少爱奇艺公司的视频广告收入,导致爱奇艺公司和极科极客公司在商业利益上此消彼长,使本不存在竞争关系的爱奇艺公司与极科极客公司因此形成了竞争关系。极科极客公司以双方所处行业不同为由否认具有竞争关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
【15】《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16】法释〔2022〕11号(2022年3月22日通过,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17】根据灼识咨询(China Insights Consultancy, CIC)按商品交易总额(Gross Merchandise Value,简称GMV)统计,2022年中国国内汽车服务市场规模为人民币1.24万亿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93万亿元,2023-2027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9%。此外,国内的平均车龄到2022年已超过6年,预计到2027年有望达到8年,复合年增长率为5%。预计中国车主在独立后市场门店购买汽车服务的单车年度开支将由2022年的人民币2102.3元增至2027年的人民币3001.0元,复合年增长率为7.4%。参见开源证券,途虎:国内汽车独立售后服务市场龙头,先发优势显著——港股公司首次覆盖报告(2024年1月17日),第15页。
【18】固然现行法与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了由法院酌定损害赔偿的选项,但必须作为特殊例外与不得已才适用的最后手段,不是让例外取代原则反成常态,让当事人竟然还可借此推卸其本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法院,变成法官的负担,浪费诉讼资源;尤其诉讼当事人皆为具有相当规模、资质的法人(经营者)时,更没有理由让其可以轻易逃避举证还能获偿。未来容有必要将此精神、要求和限制纳入法规修改,以回归正轨。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第4款(自2025年10月15日新法施行改列为第22条,内容除条文序号分别加一外,其余不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法释〔2022〕9号(2022年1月29日通过,自2022年3月20日起施行)。
【19】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road Co., 248 N.Y. 339, 162 N.E. 99 (1928); Overseas Tankship (U.K.) Ltd. v. Morts Dock and Engineering Co. Ltd., [1961] UKPC 2, [1961] AC 388, [1961] 1 All ER 404 (a/k/a Wagon Mound (No. 1) case); Lungowe v. Vedanta Resources plc, [2019] UKSC 20. Cf.,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Liability for Physical & Emotional Harm § 29 (2010).
【20】H. L. A. Hart and Tony Honoré, Causation in the Law (2nd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at chapters 15, 17;对本书第一版(1959年出版)的书评与批判,参见John H. Mansfield, Hart and Honore, Causation in the Law, 17 Vanderbilt Law Review 487 (1964), at: https://scholarship.law.vanderbilt.edu/vlr/vol17/iss2/6;另参见王泽鉴,《民法丛书:侵权行为法》,台北:作者自行出版、三民书局经销(2009年7月),第226-175页。
【21】闫妍,京东养车50亿补贴更名“震骨价”,《新浪科技》,2025年8月11日,载于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5-08-11/doc-infkraww8795617.shtml。
作者:孙远钊
编辑:Sharon



